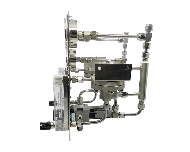最近,幾位朋友和我談到同一個(gè)話題:為我們科技的未來擔(dān)憂。
這種擔(dān)憂不是沒有道理的:科技界的一些頭面人物,思想往往太膚淺。曾經(jīng)有過多次,我聽院士級(jí)大咖報(bào)告時(shí),感到火氣上撞。直接的感覺是,他們的報(bào)告膚淺且乏味。我曾經(jīng)對(duì)朋友講:他們自己講得津津有味,我聽著就是給小學(xué)生科普。這不是聽眾水平低,而是做報(bào)告的人水平低。
有人可能會(huì)問:膚淺有錯(cuò)嗎?我的回答是肯定的。在科技界,一知半解往往比一竅不通還要可怕。一竅不通,可能喪失一些機(jī)會(huì);膚淺的理解,則會(huì)帶來錯(cuò)誤的行動(dòng),讓企業(yè)死得更快、讓國家損失更大。
在科技創(chuàng)新的領(lǐng)域,人們的競(jìng)爭(zhēng)如同與高手對(duì)弈。如果思考的步子少了,則會(huì)在競(jìng)爭(zhēng)中必輸無疑。正如孫子所言:“多算勝、少算不勝”。思考得深,就一定要“多問幾個(gè)為什么”;而我們的一些大咖,恰恰沒有“多問幾個(gè)為什么”的習(xí)慣。
比如,談數(shù)字孿生“是什么”的時(shí)候,就該問自己:為什么過去不提出來?與模型有什么不同?與CPS有什么差異?為什么要用數(shù)字孿生做仿真?
我們知道,對(duì)于企業(yè)來說,創(chuàng)造價(jià)值才是根本。而創(chuàng)造價(jià)值意味著產(chǎn)出大于投入,而不僅僅是口號(hào)。于是我們要問:這一點(diǎn)到底能不能做到?人們宣傳的價(jià)值,有那么大嗎?
實(shí)踐反復(fù)證明:凡是事先沒有把價(jià)值創(chuàng)造的邏輯想清楚的項(xiàng)目,最終往往無法創(chuàng)造價(jià)值;最終能夠創(chuàng)造價(jià)值的,都是事先想清楚再做的。就像孫子說的:“勝兵先勝而后求戰(zhàn),敗兵先戰(zhàn)而后求勝”。
據(jù)說,解決技術(shù)問題的時(shí)候,需要問到5-7個(gè)“為什么”才行;而解決理論問題的時(shí)候,可能要問到10個(gè)以上的“為什么”才行。到不了這個(gè)深度,很可能就會(huì)誤導(dǎo)聽眾、誤導(dǎo)國家。這是科技創(chuàng)新的特點(diǎn)所決定的。因?yàn)閯?chuàng)新的成功者,往往是思考更深的人。
我搞技術(shù)創(chuàng)新多年,有一個(gè)經(jīng)驗(yàn):在數(shù)字化轉(zhuǎn)型領(lǐng)域,采用先進(jìn)技術(shù)的困難往往是經(jīng)濟(jì)問題。換句話說:如果用戶提出的要求是現(xiàn)實(shí)可行的,技術(shù)上幾乎總能找到辦法;反之,如果找不到辦法,就不是工程技術(shù)問題。這樣,問題的關(guān)鍵往往是:能否找到在經(jīng)濟(jì)上劃算的方法。摩爾定律的偉大意義,就是降低了信息通信技術(shù)的使用成本;而互聯(lián)網(wǎng)平臺(tái)、SAAS軟件的本質(zhì)價(jià)值,也是降低相關(guān)技術(shù)的成本。
經(jīng)濟(jì)問題是個(gè)涉及非常廣泛的問題。成本、質(zhì)量、效率、安全、穩(wěn)定、環(huán)保等多個(gè)方面,都可以歸結(jié)到經(jīng)濟(jì)問題??紤]技術(shù)問題時(shí),一定要學(xué)會(huì)從經(jīng)濟(jì)角度考慮問題。例如,數(shù)字化、網(wǎng)絡(luò)化促進(jìn)“協(xié)同、共享、知識(shí)復(fù)用”,這三點(diǎn)是與經(jīng)濟(jì)直接掛鉤的,就是從經(jīng)濟(jì)角度看技術(shù)。
技術(shù)問題本質(zhì)是經(jīng)濟(jì)問題。進(jìn)一步,經(jīng)濟(jì)問題最終是應(yīng)用場(chǎng)景的問題:把技術(shù)用到合適的場(chǎng)景,才能創(chuàng)造價(jià)值。應(yīng)用場(chǎng)景的問題,往往是企業(yè)發(fā)展水平的問題;企業(yè)發(fā)展不到一定水平,就難以找到合適的場(chǎng)景。企業(yè)發(fā)展水平,往往是市場(chǎng)需求的問題;為技術(shù)買單的,最終是用戶。市場(chǎng)需求的問題,與社會(huì)和市場(chǎng)的發(fā)展有關(guān)。社會(huì)和市場(chǎng)的需求,往往與制度設(shè)計(jì)有關(guān);制度設(shè)計(jì)與人的利益有關(guān)......
最近,袁隆平先生去世,舉國悲痛。袁先生貢獻(xiàn)巨大、品格高尚,令人高山仰止。除此之外,袁先生這樣的科技工作者太少也是原因之一。人們敬仰先生,也反映了社會(huì)對(duì)優(yōu)秀科學(xué)家的渴望。與袁老相反,許多科技界的精英人物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,在現(xiàn)實(shí)中只會(huì)誤導(dǎo)國家、政府和企業(yè)的決策。這讓我們對(duì)中國科技的未來感到擔(dān)憂。
他們的思維膚淺,本質(zhì)上是缺乏批判性思維這種基本的科學(xué)素養(yǎng)。頭面人物不善于批判性思維,怎樣帶動(dòng)國家科技的發(fā)展?缺乏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和習(xí)慣,也是我國古代沒有發(fā)展出現(xiàn)代科學(xué)的根源。人們更擔(dān)憂的是:這些思維膚淺的人,怎么就成了國內(nèi)的頭面人物?這意味著,我們的選拔和用人制度出了毛病。這其實(shí)是更加令人擔(dān)憂的問題。
不過,盡管中國科技界有各種問題,還是有希望的。希望在于一些資歷淺的年輕人、在于民營企業(yè)的發(fā)展。華為沒有院士,照樣能成為非常優(yōu)秀的科技企業(yè)。這種現(xiàn)象值得欣慰。許多案例,就像腐土中冒出的綠芽,讓我們看到希望。我昨天在貴陽,擔(dān)任工業(yè)APP大賽的評(píng)委。在這些項(xiàng)目中,更加堅(jiān)定了我的這種認(rèn)知。
作者:郭朝暉(工學(xué)博士,教授級(jí)高工。企業(yè)研發(fā)一線工作20年;優(yōu)也科技信息公司首席科學(xué)家;東北大學(xué)、上海交大等多所院校兼職教授。國內(nèi)知名智庫、走向智能研究院的發(fā)起人之一。原寶鋼研究院首席研究員)